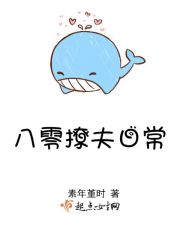古筝小说>时光为证伴你成长 > 心照与殊途(第2页)
心照与殊途(第2页)
她终于看不下去,出声打断,语气带着点不耐烦,又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你好好坐着,别动!还是我来吧。
”奇怪的是,听她这么一说,文时默竟然真的停下了手上有些野蛮的动作,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好像这事儿,本来就该她来做一样。
这种莫名的信任感来得毫无道理,却又如此自然。
李疏影不再多言,动作利落地拿起旁边桌上准备好的新纱布、棉签和消毒药水。
她凑近了些,小心翼翼地开始处理他头上的伤口。
她的手指很轻,动作却异常精准和熟练,避开最痛的地方,轻柔地剥离旧纱布,清理血痂,涂抹药膏,最后用新纱布重新包扎。
文时默就那样静静地坐着,闭上眼睛,任由她摆布。
他甚至能感受到她清浅的呼吸拂过自己的发梢。
整个过程流畅得不可思议。
还别说,她的手法特别专业,缠绕的力道恰到好处,既牢固不会松散,又不会过紧让人不适,最后打结收尾,甚至比在医院时护士包扎的还要工整和美观。
在她宣布“好了”之后,文时默忍不住抬手轻轻摸了摸头上堪称“艺术品”的包扎,终于问出了那个盘旋已久的问题:“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李疏影正在收拾医药垃圾,闻言头也没抬,用她那标志性的、带着点小得意的语气回道:“你猜啊?”文时默看着她,认真地总结了一下他目前的观察:“你好像什么都会。
会唱歌,会处理伤口,”他顿了顿,想起她那诡异的身手,补充道,“还会打架。
”李疏影将垃圾丢进垃圾桶,拍了拍手,转过身,脸上又挂上了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仿佛笼罩在一层迷雾里。
“没办法,”她耸耸肩,语气半真半假,“生活所迫,技多不压身嘛。
”这个回答,显然没有透露任何有效信息。
但文时默没有再追问。
他知道,对于这个谜一样的女人,有些答案,急不来。
她愿意出现,愿意帮他,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信号。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待她主动揭开谜底的那一刻。
慕容墨染和慕容衿雪经过那次深入骨髓的交心谈话后,房间里那种无形的隔阂与猜疑终于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壮的、并肩作战的默契。
两人轮流进入浴室,用温热的水流洗去一身疲惫与从别墅带出来的污浊气息,然后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关掉了灯。
没有再多言语,她们都知道,从明天开始,将面对的是什么。
此刻,她们需要的是绝对的休息。
巨大的情绪波动和一天的奔波早已耗尽了她们的精力,几乎是头一沾枕头,两人便陷入了沉沉的睡眠,开始为未知的征程养精蓄锐。
在她们离开文家老宅,最后一次去询问文时默下落的时候,文母看着这两个执拗的女孩,尤其是慕容墨染那仿佛找不到人就绝不独活的绝望眼神,最终还是心软了。
她趁着文父不注意,将慕容衿雪拉到一边,用极低的声音,快速而清晰地透露了最关键的信息:“他去了g市。
更多的,阿姨也不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