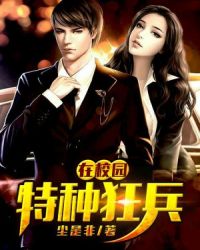古筝小说>四合院木匠的烟火人间最新章节更新时间 > 第181章 考试(第2页)
第181章 考试(第2页)
林墨起初还会解释一句自己是土木系大四本科生,但次数多了,见教授们往往先入为主,他也就只是微微一笑,不再刻意纠正,将全部心神都投入到对问题的探讨与求解之中。
因为林墨的年纪也比同年级的同学要大许多,一时间土木系有个特别厉害的研究生,到处跨系请教问题”的说法,在相关院系的教师圈子里悄悄流传开来。
无人想到,这个被误认为研究生的年轻人,只是一个在本科毕业设计的阶段,便已凭借其惊人的求知欲和扎实的功底,提前闯入了更高学术领域的大四学生。
窗外,雪落无声。林墨穿梭于不同的系馆之间,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他的“虚实建造场”中的联合体蓝图,在无数次的请教、推演与优化中,日趋完善与精密。
而他的内心,也在这不断的“问道”过程中,变得更加沉静、充实与自信。
六四年的一月中旬,四九城寒意正浓,水木大学却迎来了学年中最紧张炽热的时刻——期末考试周。
校园里静默了许多,往日喧闹的操场和林荫道变得空旷,所有的生机与活力仿佛都浓缩在了图书馆通明的灯火下、自习室沙沙的翻书声与笔尖划过纸面的急促声响里。
对于大四的学生而言,这或许是本科阶段最后一次为理论试卷而搏杀。空气中弥漫着茶叶与风油精混合的提神气味。
然而,在这片普遍性的焦虑中,林墨却显得格外沉静。他的复习节奏依旧规律,神情不见半分紧张。当一门门专业课的考卷发下,他审题、思索、落笔,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无论是需要复杂计算的结构力学,还是涉及大量记忆的施工规范,抑或是需要综合分析的工程经济,都无法在他笔下形成真正的阻碍。
所有与动手实践、设计应用紧密相关的课程都是现场公布成绩,毫无悬念,林墨均以接近满分的成绩高居榜首。让班甚至同年级的同学一阵惊叹。
期末考试的战鼓余音未歇,另一场关乎技艺巅峰认证的考验已接踵而至——七级木工考核,在位于城东的轻工局直属考核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考核现场气氛庄重而肃穆。来自各大厂矿的顶尖木工高手齐聚于此,其中不乏两鬓斑白、眼神锐利的老匠人。龙成厂的赵山河也赫然在列,他面色沉静,目光在与自己徒弟林墨交汇时,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
当考核委员会宣布最终实操考题时,现场响起一片低低的吸气声。题目极具挑战性——在规定时间内,独立设计与制作一件用于大型风机的精密铸造的“工业母模”核心部件。
该部件形态复杂,非规则曲面与内部加强筋交错,要求不仅尺寸公差、形位公差控制在极严格的范围内,更对表面光洁度、整体结构稳定性以及木材的预处理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这已不仅仅是考验“手艺”,更是对设计能力、材料学理解、力学把握乃至现代工业化生产需求的综合考量。
林墨立于分配给自己的工位前,神色无波。他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先仔细审阅图纸要求,手指在光洁的木料上轻轻拂过,闭目凝神。
下料、刨削基准面、划线……他的动作并不快,却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感和绝对的精准。刻刀、圆凿、异形刮刀在他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
遇到那些极其复杂的内部曲面和筋位时,他并未完全依赖电动工具,更多是凭借那双经过健体操千锤百炼的手,进行精微的手工塑造。手腕的每一次抖动,指尖的每一次发力,都恰到好处,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欠。
他甚至在制作过程中,依据自己对木材物性和受力逻辑的理解,对图纸上某处他认为可能存在应力集中的过渡区域,进行了微小的、却更为合理的弧度优化。
在处理木材时,他采用了自行配比的混合树脂进行局部浸渍强化,以应对铸造环境下的温湿度变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考场内充斥着各种工具的声响,空气中木屑飞扬。林墨始终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心无旁骛。当最后一道用特制抛光膏配合高目数砂纸完成的抛光工序结束,他将那件泛着温润光泽、线条流畅而充满力量感的母模部件轻轻放在检测台上时,引来了全场瞩目。
负责检测的是几位部里资深的老专家和八级工老师傅。他们拿着高精度量具、光学投影仪,反复测量、比对,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严肃审视,逐渐变为惊讶,最终化为毫不掩饰的赞叹。
“整体尺寸公差稳定在±0。15毫米以内,关键定位面平面度误差小于0。05毫米……”
“曲面光洁度……达到镜面效果!”
“内部加强筋布局合理,与外壳连接处过渡自然,毫无应力痕迹……”
“木材处理得当,含水率均衡,稳定性极佳……”
一项项检测结果报出,每一项都远超考题设定的优秀标准。几位老专家围着那件作品,低声交流着,不时投给林墨复杂难言的目光。那不仅仅是满意,更是一种对后生可畏的震撼与期许。
结果毫无悬念。林墨以无可争议的超高分数,一举通过七级木工考核,成为当年考核中最为耀眼的新星。而另一边,赵山河也凭借其深厚无比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顺利通过了七级考核。师徒二人,在同一考场,双双晋升七级,成就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