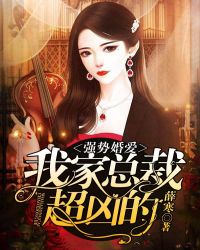古筝小说>四合院木工手艺人立地为秋 > 第129章 技艺与年关(第2页)
第129章 技艺与年关(第2页)
他甚至向系里申请,将一门课程设计的模型制作部分,完全按照实际工程标准来完成,并主动编写了详细的物料清单、工艺流程图和工时预算表,交给了指导老师,作为“项目统筹”的练习。老师看完后惊讶不已,这份计划的周密程度远超学生作业的水平!
夜晚,则在工坊内进行最精密的修行:利用双倍时间,雕刻那些复杂如艺术品般的异形构件;推演斗拱模型在不同荷载下的应力分布;
他的大学生活,由此进入了另一种极致的充实。在同学眼中,他愈发深沉低调,除了图书馆、实验室、木工机房,几乎不见踪影。但所有与他合作过项目的人都清楚,这个沉默的年轻人,体内蕴藏着的专注力与执行力。
时光飞逝,转眼又是岁末。1961年的农历除夕,在连续数日的凛冽北风和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如期而至。
四合院再次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屋檐下挂满了冰凌。天气酷寒,但比起去岁今朝那蚀骨入髓的饥饿与绝望,今年的除夕,院里总算多了几分硬撑下来的“稳当”和习惯性的清冷。
各家的年货,依旧透着股捉襟见肘的算计。粮站定量未见增加,黑市物价依然高企,所谓“年味”,更多是依靠夏秋时攒下的一点存货和精打细算。
傻柱依旧靠着厨艺和时不时进山的收获,让家里飘出炖肉的香气。他依旧给聋老太太送吃的,贾家依然是获得“接济”的大头。
许大茂家关起门来享受着娄家源源不断的“补给”,香气被厚门帘紧紧锁住。闫埠贵家的年夜饭依旧是“计算”的典范。
贾家今年桌上总算见了点荤腥,得益于傻柱的奉献和贾东旭死后抚恤工资。但一个小婴儿槐花的出生,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麦乳精、糖票都是巨大的开销。
秦淮茹脸上难见喜色,只有深深的疲惫。贾张氏居然还胖了些,盘算着怎么从儿媳手里多抠出几毛钱。
后院刘海中家,大儿子刘光齐今年依旧没回来,只拿一些粮票和物资,二大爷的脸色因此阴沉了许久。刘光天在厂里依旧学徒,但似乎踏实了些。前院杨大山家,孩子依旧瘦弱,李贤英和程秀英相互扶持,日子清苦但有了盼头。
大雪无声落下,掩盖了院中的泥泞,也暂时抚平了各家的愁苦与算计。零星的鞭炮声在空旷的雪夜里显得格外清脆,却也格外稀疏。家家户户窗棂透出的昏黄灯光,映照着忙碌准备年夜饭的身影,构成这个困难年代四合院特有的、坚韧而清冷的年关图景。
与院里大多数人家相比,林家今年除夕的气氛,却要温暖踏实得多。
林贤的顺利工作,如同给这个家注入了一股坚实的底气。虽然只是个初级技术员,工资在四合院除了几个中高级工已经算中坚,那是国家发的、月月都有的固定收入,是城里人的身份象征,是未来可期的起点。意味着遇到急事家里能拿出一笔活钱。
程秀英的脸上是掩不住的宽慰和喜气。她早早地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家具陈旧,但窗明几净。
林墨带回来的野物和从“学校”换来的干货,林贤用第一个月工资特意买回的一条五花肉、一瓶二锅头和几挂小鞭炮,让林家的年货前所未有地“丰盛”起来。
傍晚,小厨房里热气蒸腾。程秀英掌勺,林墨打下手,林巧帮着剥蒜洗菜,林贤则负责照看炉火。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旁边蒸着白面掺和白面面的饺子,林墨用带来的山鸡和蘑菇炖了一锅鲜美的汤,以及山羊肉等几个菜。
虽然比不上富贵人家,但在这个年月,已是难得一见的丰盛晚餐。
饭菜上桌,香气四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脸上都洋溢着真切的笑容。
“来,都满上!”林贤有些激动地给母亲、哥哥、妹妹和自己都倒上一点点白酒,“妈,哥,巧儿,祝咱们家新的一年越来越好!祝妈身体健康!祝哥学业进步!祝巧儿学习好!”
“好,好!”程秀英眼圈微红,笑着点头,“我祝我两个儿子工作顺心,学业有成!祝我闺女平安长大!”
林墨也举起杯:“祝我们家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都平平安安!”
就连林巧也学着大人的样子,举起盛着糖水的小碗,脆生生地说:“祝妈妈哥哥都高兴!”
温暖的灯光下,一家人吃着、笑着、说着家常。屋外是冰天雪地,寒风呼啸,屋内却暖意融融,亲情流淌。饭菜的热气模糊了窗上的冰花,也模糊了程秀英欣慰的泪水。这一年所有的艰辛与担忧,仿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慰藉。
吃过晚饭,林贤兴致勃勃地带着林巧到院子里放鞭炮。小小的鞭炮声在雪夜里噼啪作响,映照着兄妹俩冻得通红却满是欢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