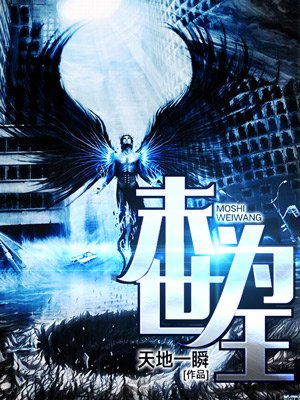古筝小说>四合院木工手艺人立地为秋 > 第133章 分享与困境(第1页)
第133章 分享与困境(第1页)
随后,林墨开始了他关于“基于简易人体测量的家具尺寸适配性研究”和“人造板在不同家具部件中的应用优势与工艺适配性”的分享。
他的发言数据清晰、案例具体,比如展示了如何通过几个关键身体尺寸的测量来推导出更合理的椅子和桌子高度,也详细分析了人造板在柜体、背板等部件上应用如何节省木材、提高稳定性。发言得到了在场许多工艺师和厂长的频频点头。
刚刚分享完,张思远率先发难,试图用“艺术性”和“传统”来质疑:
“林墨同志,您分享的数据和应用案例确实很……‘科学’。”他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讽
“但是,家具不仅仅是功能的容器,它更是承载着文化和审美情感的艺术品。您这种过于依赖数据和标准化尺寸的方法,会不会导致设计出来的家具冷冰冰的,缺乏人情味和艺术的温度?”
“而且,广泛使用人造板这类‘代用品’,是不是也背离了我们工艺美术追求‘真材实料’、‘匠心独运’的传统精神?”
林墨平静回应:“张同志,您说的艺术性和传统精神很重要。但我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使用者来说,一件家具最先、也是最持续的‘人情味’,来自于它用起来是否舒适、顺手,是否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更轻松。
一把尺寸不合适的椅子,即使用最名贵的木材、最精美的雕花,坐上去腰酸背痛,恐怕也难言‘艺术’的享受。我们的研究,正是为了让家具更好地‘服务’于人,这种基于人体尺度的‘舒适’,难道不是最深层次的‘人情味’吗?”
他环视会场,说道:“这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能显着节约珍贵的天然木材,尤其是大规格板材,这对保护国家森林资源意义重大;”
“第二,人造板抗变形能力其实优于许多实木,能提高产品的整体稳定性;”
“第三,能有效降低成本,让更多家庭能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耐用家具。这不是牺牲品质,而是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对材料更合理、更高效的应用,最终实现的是社会效益和用户实惠的双赢。我们不能因为技术不足,就否定一种材料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它在当前阶段的合理应用价值。”
张思远不甘心地做最后挣扎:
“即使如您所说,但这些标准化的尺寸、替代性的材料,最终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家具失去地域特色和手工艺的独特美感?大家都用一样的尺寸、一样的板材,那北京的家和上海的家还有什么区别?工艺美术的‘美’又何在?”
林墨微笑,给出致命一击:“张同志,基本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尺寸是舒适的‘基石’,它并不会限制‘美’的发挥。就像写字,笔画顺序是基础,但最终能写出楷书、行书还是草书,写出什么样的风骨,靠的是设计师的功力。”
“人造板作为内部基材,也并不妨碍我们在表面处理、造型设计、细节装饰上融入地方文化元素和传统工艺精髓。我们的‘东方韵律’系列,很多部件也考虑了标准化生产,但它的外观和神韵,谁又觉得失去了东方特色呢?”
他总结道:“我的观点是用科学的方法确保‘好用’和‘经济’这个基础,用艺术的思维去创造‘好看’和‘有文化’这个上层建筑。
两者结合,才能设计出既让人民群众用得起、用得舒服,又能体现我们文化自信的好家具。”
“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特’美感,就忽视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和大多数人的可及性。请问,是让千家万户都用上舒适耐用的家具更重要,还是坚持某种抽象的、可能只有少数人欣赏的‘手工艺独特美感’更重要?”
林墨用“基石与上层建筑”的比喻清晰划分了“功能基础”和“艺术表现”的关系,并以“东方韵律”的成功作为实证。最后用一个尖锐的选择题收尾,将对方置于忽视人民基本需求的位置上,使其观点在政治和道义上彻底失分。
张思远和陈敏面对这个选择题,哑口无言,再也无法反驳。
王副司长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接下来的会议中,林墨又就胶合板的应用潜力、基于基本人体尺寸的家具尺度的建议做了简短分享,内容务实,数据支撑清晰,引用的国内外资料出处也明确,再次赢得了在场大多数务实派工艺师、厂长们的认可和称赞。
研讨会结束后,不少人主动过来与林墨交换联系方式,探讨合作可能。那位设计室主任更是拉着他的手说:“小林同志,以后要多来我们所里交流,你的很多想法,既新又实,对我们启发很大!
研讨会上的风波并未在林墨的生活中留下太多涟漪。于他而言,那更像是一次对自身设计理念和实践成果的检验与梳理。当争论声散去,他依旧回归到水木园那紧张而充实的节奏中,教室、图书馆、汽车楼工作室、发动机课题组,四点一线,规律如钟摆。
在发动机研究小组,林墨制作的精密木模发挥了巨大作用。孙志远等人根据流场测试结果不断优化进气道和燃烧室的设计,而林墨总能迅速地将二维图纸转化为可供铸造或实验的实体模型,其精度和还原度极大缩短了试错周期
。李老师喜上眉梢,连连感慨林墨的双手“抵得上半个实验室”。项目的推进速度远超预期,一篇关于新型气道优化方案的论文初稿已然成型,孙志远甚至私下表示,如果效果持续向好,或许能在毕业前争取到一个联合署名的机会。
林墨对此淡然处之,于他而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形”、“力”、“流”理解的深化,是通往更高技艺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