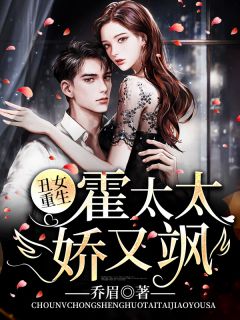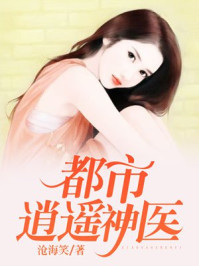古筝小说>四合院木工手艺人立地为秋 > 第154章 生活琐事下(第1页)
第154章 生活琐事下(第1页)
贾家还在闹腾的时候,此时的傻柱家却俨然成了棒梗的“避风港”和“游乐天地”。因着傻柱隔三差五的接济,更因他那屋里总飘着别家没有的油腥味儿和零嘴香,棒梗往那儿跑得愈发勤快,几乎成了半个家。
傻柱自己呢,年岁虽长,却存着几分半大孩子的心性。相亲屡屡受挫,妹妹何雨水又住校在外,他一个人守着空落落的屋子,难免寂寞。棒梗这个邻家小子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这份空虚。他对棒梗,与其说是长辈对晚辈的照拂,不如更像是个孩子王带着小跟班。
有时从兜里摸出几颗水果糖、半把瓜子,有时兴致来了,甚至会把当年在天桥底下、胡同旮旯里,从三教九流那儿看来的、学来的一些“本事”,当做趣闻显摆给棒梗看。
“嘿,小子,看好了,这招叫‘燕子抄水’,手法要快,眼神得准!”傻柱往往会带着几分得意,在屋当间比划两下似是而非的把式,身形扭动间带着江湖艺人特有的夸张。
“看见这锁头没?看着铜墙铁壁,其实窍门在这儿,找个硬铁片,找准地方这么轻轻一捅……”他或许只是无聊至极,顺嘴秃噜,将一些溜门撬锁的旁门左道当成了显摆能耐的谈资,全然未顾及听者有心。
棒梗这孩子,天生几分小聪明,可惜在贾张氏无原则的溺爱和家庭缺乏正确引导的环境下,那点聪明劲儿难免用错了地方。他觉得傻叔这些“本事”又新奇又厉害,透着股书本上没有的、野路子出来的“能耐”,比课堂上那些之乎者也有意思多了,便暗暗记在心里,私下里有样学样。
这一切,都被院里的壹大爷易中海默默地看在眼里,他心中的矛盾与焦虑如同藤蔓般日益滋长、缠绕。一方面,傻柱乐于接济贾家,与贾家关系亲近,这本是他乐于见到的局面。
这完美契合了他极力维持的“邻里互助”、“照顾孤儿寡母”的道德标杆人设,也能让秦淮茹和孩子们念着他的好。在他长远的谋划里,这正是将傻柱和贾家未来捆绑在一起,为自己养老大业添上的一道“双保险”。棒梗是贾东旭的儿子,是他的徒孙,于情于理,多受些照拂也是应当的。
但另一方面,傻柱和贾家走得实在太近了,尤其是傻柱对秦淮茹那种近乎本能的维护,以及两人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微妙气氛,再加上傻柱对棒梗那种毫无原则、近乎纵容的宠溺,都像一根根细刺,扎在易中海的心头,让他隐隐感到不安。
他几次三番给傻柱介绍对象屡屡失败,固然有他暗中作梗、生怕找个厉害媳妇脱离掌控的原因,也有傻柱很多心思扑在了接济贾家、逗弄棒梗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易中海内心深处渴望傻柱尽快成家立业,娶一个他看来“老实、可控”的媳妇,然后他才能以“恩人”和“长辈”的身份,顺理成章地介入并主导傻柱的小家庭,完成从“备用养老人”到“正式养老人”的身份过渡与交接。
可眼下,傻柱的心,仿佛被贾家,特别是被那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秦淮茹,给牢牢拴住了。这让他精心布局多年的计划,出现了偏离轨道的危险迹象,一种掌控力流失的焦虑感时常攫住他。
“得找个机会,再跟柱子好好谈谈了,不能让他再这么糊涂下去。”易中海背着手,站在自家窗前,望着窗外四合院上空那片被屋檐切割得四四方方、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
“也得适时地敲打敲打淮茹,让她明白,她能留在城里,有这份稳定的工作,靠的是谁的帮扶。不能让她……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坏了规矩。”
屋外,腊月的寒风依旧在四合院的廊檐屋角间穿梭呼啸,卷动着各家门廊上厚重的棉布帘子,发出噗噗的声响,也卷动着这方小天地里,人心深处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精细算计、隐隐焦虑和正在悄然滋长、不知何时会爆发的隐患。
这个冬天,对于南锣鼓巷95号院的许多人来说,注定了不会平静。
时间的脚步悄然跨入一九六二年的岁末,水木大学在几场纷纷扬扬的冬雪覆盖下,结束了期末的紧张考核。随着最后一门课的答卷上交,校园里持续已久的紧绷气氛骤然松弛,被一种归心似箭的躁动与喜悦所取代。
学生们提着大包小裹,陆续踏上返乡的旅程。林墨送别了沈知书、王建国等一众室友,却并未立刻收拾行装返回南锣鼓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