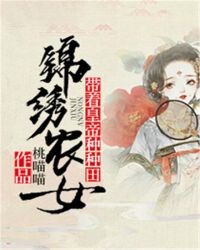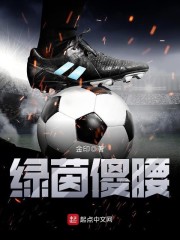古筝小说>四合院小木屋 > 第167章 暴雨(第1页)
第167章 暴雨(第1页)
八月初的四九城,天色沉郁如墨,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在屋檐上,闷雷在云层深处翻滚。一连几天,暴雨如注,仿佛天河倾泻,将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片湿漉漉的水汽之中。
林墨因为大雨困在家中,他并没有闲着,而是趁此机会,将进入“鲁班工坊”,全心投入那座依梁先生手稿所制的“重檐十字脊亭”最后的组装。
亭阁结构繁复,十字脊交汇处榫卯咬合需分毫不差,重檐起翘的弧度更是全凭手感微调。林墨心神沉浸,刻刀轻移间,木屑纷落,最后一个构件严丝合缝地嵌入预定位置。
看着整座亭阁顿时气韵贯通,静立于工坊中央,虽然是缩比模型,却能看出原来的具凌云之势。
就在这时,外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易中海那带着焦急的洪亮嗓音:“大家都出来看看!雨水快漫过门槛了!”
林墨心神一动,退出工坊,推开房门。只见院中积水已没过脚踝,浑浊的雨水打着旋儿向低洼处汇聚。易中海正披着蓑衣,站在垂花门下,指着院门外那条已成小溪的胡同,脸色凝重。几位大爷和闻声出来的邻居也都聚在廊下,议论纷纷。
林墨没有多说,快步走到四合院大门口,目光打量着那两扇厚重的木门门槛,以及门轴下方的石臼。他返身回家,取来皮尺和自制的水准尺,不顾雨水淋湿,仔细测量了门槛高度、门轴间隙以及门外地势坡度。
回家后,他铺开纸张,略一思忖,便画出一种可快速拆装的挡水板结构图。板材选用家中备用的厚实松木,利用榫槽拼接,内侧加设三角支撑,确保能承受一定水压。
他手下极快,刨锯凿削,不过半个多小时,四块长度合宜、边缘带着防水槽的挡水板已经制成。
当他将挡水板扛到门口时,易中海眼睛一亮,立刻招呼阎埠贵、刘光天等几个壮劳力帮忙安装。挡水板严丝合缝地卡在门槛内侧,易中海又组织人手,用早就备好的麻袋装土,在挡水板内外两侧及中间缝隙处层层填实、踩紧,形成一道坚固的临时堤坝。
同时,安排院里的大人,用盆、桶不断将淋进院内的雨水泼洒出去,而自己则带着几个壮劳力检查漏水的墙壁和,检查有没有要倒的墙。众人齐心协力,暂时将不断上涨的雨水挡在了大门之外。林墨也回家将要返水的厕所堵了起来。
眼见雨势毫无停歇之意,而院中的水势控制住了以后,林墨心系师父赵山河以及王铁等几位长辈。他披上厚重的油布雨衣,跟院中指挥的三个大爷交代了一下,就带上工具和几块预先按通用尺寸做好的挡水板料,冒着倾盆大雨出了门。
雨水如帘,视线模糊,街上积水已没过小腿。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先后赶到几位长辈家中,依据各家门槛具体情况,现场调整、安装挡水板。
师父赵山河已经做好的挡水板,他则帮忙安装,师父嘴上没说什么,眼神里却满是赞许,师母临别时硬塞给他一壶驱寒的老酒。
等林墨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南锣鼓巷时,胡同里的积水已然没过膝盖,水流湍急。他艰难地挪回95号院,只见院内情形比之前更为紧张。
雨水虽然被大门处的土袋堤坝挡住大半,但持续的暴雨和高处汇流而下的积水,仍不断从院墙根、排水口等处渗入,院内积水仍有齐踝深。更令人担忧的是,几户年久失修的人家开始漏雨,闫埠贵家和杨大山家的屋顶甚至出现了小范围的塌陷湿痕。
易中海、刘海中两位大爷此时也顾不得平日架子,亲自指挥。傻柱、许大茂、刘光齐、闫解成等年轻人被分派任务,上房检查、用油毡临时遮盖漏点,或用木柱加固看似危险的房梁。
林墨一回来,立刻因其精湛的木工手艺成了主力。他爬上爬下,查看檐檩、修补椽子、加固榫卯,动作沉稳利落,引得众人连连称赞。
各家各户屋内都已进水,程度不同。人们慌忙将粮食、被褥、贵重物品等搬到桌上、柜顶,甚至学贾家那样,用绳子吊上房梁。只有林家,因林墨早两年的改造,搭建了坚固的阁楼。此时程秀英和林巧早已将重要物什转移至阁楼,地面虽也漫入些许积水,损失却是全院最小。
及至傍晚,雨势稍缓,各厂矿也陆续传来因暴雨放假的通知。院里众人终于能稍喘口气,但看着满屋狼藉和依旧阴沉的天空,脸上都写满了愁苦。
暴雨肆虐了两日一夜,终于在天明时分渐渐停歇。
天色放亮,积水开始缓慢退去。四合院里一片泥泞,家家户户都忙着清理屋内的积水和淤泥,将被水泡过的家具物什搬出来晾晒,院子里挂满了湿漉漉的衣物被褥,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和霉变的气味。
午后,胡同及街道上的积水基本退去,露出了被大水冲刷得一片狼藉的路面。
淤泥中,赫然可见许多被洪水从各处冲来的“浮财”——有散落的玉米、土豆、萝卜等蔬菜瓜果,有破损的锅碗瓢盆,甚至还有被冲散的木料、布匹等物甚至还有被淹死的家禽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