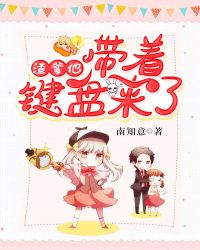古筝小说>未来星空科幻画创意说明 > 第59章 元亮别来无恙(第2页)
第59章 元亮别来无恙(第2页)
陶渊明笑着摇了摇头,往两个粗瓷碗里添满酒:"为何要离开?"他指了指院里的菊花,"它们在这里开得正好;指了指溪边的柳树,"它的影子照在水里,鱼都爱围着转;又指了指屋里昏黄的灯光,"阿妻在缝补衣裳,阿儿在数星星。这里的风是自由的,云是自由的,连泥土里的蚯蚓,都能按自己的意思钻来钻去。"
青林沉默了。他想起自己的时代,人们可以在一小时内跨越半个地球,却要提前三天申请航线许可;可以和千里之外的人全息通话,却找不到隔壁邻居说句话;可以定制任何想要的情绪体验,却在深夜里对着光脑屏幕感到彻骨的孤独。他们追求了千年的自由,是能抵达宇宙边缘的自由,却把自己困在了更精密的牢笼里。
"你们那里,没有这样的地方吗?"陶渊明好奇地问。
青林想了想,描述起悬浮城市,描述起星际飞船,描述起能模拟任何环境的全息舱。陶渊明听得眼睛发亮,却在他说完后轻轻叹了口气:"听起来,像是把天地装进了盒子里。"
那天晚上,青林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站在实验室里,看着能量矩阵的数据流在眼前流淌,却听见窗外传来孩童的笑声。他推开窗,看见桃林漫山遍野地绽放,陶渊明站在花海深处朝他挥手,衣袖上沾着金黄的菊瓣。
转眼已是深秋。青林跟着村民们收割稻谷,手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晒得黝黑的皮肤上结了层健康的光泽。他学会了用竹筐挑水,学会了在石臼里舂米,甚至能哼几句当地的民谣。有次陶渊明看他劈柴,笑着说:"青林如今倒像个真正的农人了。"
他开始明白,这里的自由不是没有约束,而是懂得与天地和解。春种秋收要依时节,刮风下雨要听天意,就连说话都带着乡音的局限。但正是这些局限,让每滴汗水都有实在的分量,每口饭都有劳作的甘甜,每句问候都带着真实的暖意。
这天清晨,青林在溪边洗脸,忽然发现水面倒映的天空裂开道熟悉的幽蓝裂隙。他的心猛地一沉,知道该回去了。
他跑回茅屋,陶渊明正坐在案前写诗,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宣纸上,墨迹洇开淡淡的晕。青林站在门口,看着那个清瘦的背影,突然说不出告别的话。
"要走了吗?"陶渊明转过头,脸上没有惊讶,只有温和的笑意。
青林点点头,喉咙发紧。
陶渊明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个布包:"这个给你。"打开一看,是包新收的菊花种子,还有半块没吃完的麦饼。"你们那里,若是有空闲的土地,不妨种种看。"
青林接过布包,指尖触到粗糙的棉布,突然想起自己的个人终端里存着千万亿字节的信息,却从未有一样东西,能像这包种子般沉甸甸的。
裂隙的引力越来越强,青林后退着走向那片熟悉的稻田,看见陶渊明站在桃林边朝他挥手,看见那个曾给他水喝的老者,看见追着蝴蝶跑的孩童,他们的身影在晨光里渐渐模糊,却像刻在了他的骨头上。
"记得,风是不要钱的!"陶渊明的声音远远传来,带着笑意。
剧烈的眩晕感过后,青林跌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警报声还在响,能量矩阵已经恢复平静,控制面板上的时间显示:2142年3月17日,14点32分——距离他离开,只过了七分钟。
同事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他发生了什么。青林张了张嘴,却发现那些关于稻田、菊花、粗瓷碗的记忆,像沾了水汽的墨痕,正在一点点淡去。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触到个坚硬的东西——是那半包麦饼,还带着微温的余韵。
那天晚上,青林没有回公寓。他避开悬浮车流,走到城市边缘那片废弃的湿地公园。月光穿过防护罩的缝隙漏下来,照在荒芜的土地上。他蹲下身,用手指刨开硬化的地面,把那包菊花种子埋了进去,又从水壶里倒出些水。
做完这一切,他坐在草地上,看着远处流光溢彩的城市轮廓。终端提示有三十七条未读消息,都是关于引擎项目的紧急汇报。但青林没有点开,只是闭上眼睛,听着风穿过铁丝网的声音——虽然带着金属的震颤,却比全息模拟的自然音效真实得多。
他想起陶渊明说的那句话:"风是不要钱的。"
也许自由从来都不在宇宙的边缘,不在精密的仪器里,而在伸手能摸到的泥土里,在抬头能看见的星空里,在愿意为一朵花开而停下脚步的时间里。青林笑了笑,第一次觉得,这个被数据和代码包裹的世界,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呼吸。
他站起身,拍了拍沾着尘土的裤子,决定明天去申请块社区菜园。毕竟,种子已经埋下了,总得等着看它会不会发芽。至于那些关于桃花源的记忆,就算终会褪色,也总会在某个起风的午后,带着淡淡的菊香,悄悄回到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