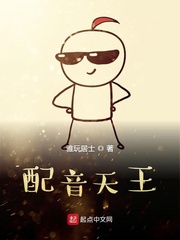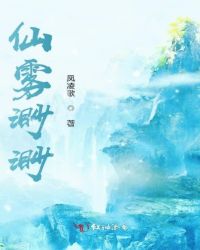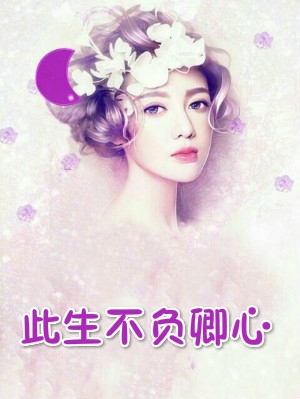古筝小说>未来星空科幻画创意说明 > 第83章 与全才共探的时空秘境(第2页)
第83章 与全才共探的时空秘境(第2页)
他拿起一个金属制的天文仪器,圆盘上刻着星图:“通过太阳的影子,这个日晷能精确到一刻钟。而这个星盘,能算出任何时刻的星座位置。”他转动仪器,金属齿轮发出悦耳的咔嗒声,“宇宙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不是吗?”
青林忍不住展示了量子记录仪里的现代科技:飞机的三视图、坦克的内部结构、机器人的电路原理图。达芬奇盯着屏幕上的喷气式发动机,手指在空气中模仿叶片转动的轨迹:“原来如此……用燃烧产生的气体推动,比人力更强劲。”他忽然在纸上画起来,将喷气发动机与他的扑翼机结合,“或许可以这样改进……”
两人常常争论到深夜。青林惊叹于达芬奇超越时代的构想,达芬奇则对未来的科技充满好奇。“为什么你的时代能造出这些?”他摩挲着屏幕上的高铁图片,“是因为有更精密的工具吗?”
“是因为有更多人站在您的肩膀上。”青林说,“您的草图启发了后来的科学家,他们不断改进,最终实现了您的梦想。”
达芬奇沉默良久,将一张未完成的飞行器图纸递给青林:“帮我看看,这个尾翼的角度是否合理?”图纸上,滑翔机的机翼呈流线型,尾翼可以调节角度,与现代滑翔机的设计惊人地相似。
离别的预兆出现在一个清晨。青林的量子记录仪发出持续的警报,屏幕上的时空坐标开始不稳定。他知道,自己必须回到未来了。
达芬奇似乎早已察觉,他将一个铜制的小盒子交给青林。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齿轮,齿纹精密,边缘刻着一行小字:“自然的奥秘藏在细节里。”
“这是自动骑士的核心零件,”达芬奇说,“留给你做纪念。或许在你的时代,它能派上用场。”他指着墙上的《最后的晚餐》草图,“我总觉得,艺术与科学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在探索真理。”
青林将量子记录仪里存储的所有现代科技资料传输到一个特制的芯片里,交给达芬奇:“这是未来人对您构想的实现。您的每一张草图,都改变了世界。”
达芬奇接过芯片,像捧着一件艺术品般郑重:“我只是记录下看到的世界。真正创造未来的,是那些不断追问‘为什么’的人。”
时空扭曲的瞬间,青林最后看到的,是达芬奇重新拿起炭笔,在《蒙娜丽莎》的画布上添上最后一笔——那抹微笑,仿佛包含了对未来的所有期许。
回到现代实验室,青林打开那个铜制盒子。齿轮的齿纹在灯光下泛着微光,与量子记录仪里达芬奇的草图比对,竟与现代直升机的减速器齿轮参数惊人地吻合。
多年后,青林在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他将量子记录仪里的影像与达芬奇的原始草图并置展出:飞行器草图旁是莱特兄弟的飞机,坦克设计图边是现代主战坦克,机器人雏形旁边则是NASA的火星探测器。
“达·芬奇的伟大,不在于他预见了未来,”青林在开幕式上说,“而在于他证明了人类的好奇心可以跨越领域、突破时代。他既是画家,也是科学家,因为他相信美与真理终将相遇。”
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那个铜制齿轮。它被放置在一个真空玻璃罩里,旁边的屏幕循环播放着青林与达芬奇在工坊里讨论的影像。无数参观者驻足凝视,看着五百年前的天才与来自未来的访客,用不同时代的语言,探讨着同样的问题——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创造未来。
青林站在角落,看着玻璃罩里的齿轮。他忽然明白,自己跨越时空带回的,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信念——那种相信人类的创造力永不枯竭,艺术与科学终将殊途同归的信念。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始于那个在佛罗伦萨的石砌工坊里,用炭笔与圆规丈量世界的全能天才,始于那个被后世永远铭记的名字——列奥纳多·达·芬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