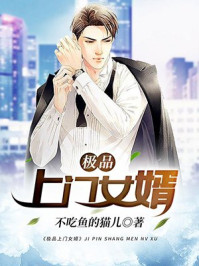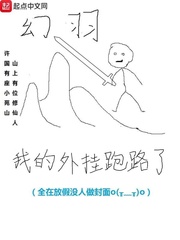古筝小说>未来星空烟还在卖吗 > 第56章 万三密码(第1页)
第56章 万三密码(第1页)
粒子对撞机的蓝光还在视网膜上闪烁时,青林已经踩着青石板跌进了一条喧闹的巷子。
鼻尖萦绕着生煎包的油香与河泥的腥气,耳边是“苏绣三尺价十两”“松江棉布论匹卖”的吆喝——他低头看了眼身上的实验服,又摸了摸口袋里那台电量仅剩1%的全息投影仪,突然明白自己闯祸了:本该定位到北宋汴京的坐标,竟错飘到了明初的苏州。
“客官要住店?”一个店小二模样的少年凑上来,指着巷口的幌子,“咱‘聚宝楼’可是苏州头一份,沈老板的产业!”
沈老板?青林心里咯噔一下。他调出投影仪里仅存的《明史》片段,指尖划过“沈万三,吴兴人,徙居苏州,富甲天下”的字句时,巷口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人群像被水流分开般退向两侧,一顶乌木轿子碾过青石板,轿帘缝隙里,他瞥见一个身着云锦的中年男子正拨弄着算盘,指节上戴着枚羊脂玉扳指,算盘珠碰撞的脆响竟盖过了周遭的喧嚣。
“那就是沈万三?”青林拽住店小二。
“可不是嘛!”少年眼里闪着光,“听说沈老板的船队能从苏州直开到爪哇国,一船胡椒能换十座宅子!”
全息投影仪突然发出低电量警报,青林慌忙按灭屏幕。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找到落脚点,而眼前这个“沈老板”,或许是解开时空错位之谜的关键——毕竟,能在洪武年间富可敌国的人,绝不会是寻常之辈。
码头的“流动”财富
三日后,青林混在搬运工里挤上了沈万三的商船。船坞里停泊着二十余艘三桅帆船,工人们正将一包包丝绸、瓷器搬上船,账房先生拿着毛笔在竹简上飞快记录,而沈万三就站在跳板旁,亲自核对清单。
“这批宋锦要送广州,”他指着最上面的包裹,“让船老大多带些苏木回来,最近南京城里的染坊都在抢。”
“苏木?”青林心里一动。他记得史料记载,明初常用苏木作为货币支付军饷,这沈万三竟能提前预判市场需求?
“你这后生看着面生。”沈万三突然转头,目光落在青林的帆布运动鞋上——这双现代鞋在布鞋堆里格外扎眼。
青林心头一紧,忙弯腰作揖:“小人从北方来,想跟着老板学做买卖。”
沈万三没追问鞋子的事,反而指着船舱里的瓷器:“知道这些碗碟为什么能卖上价吗?”
“因为是官窑出的?”
“不全对。”沈万三拿起一只青花碗,指尖敲过碗沿,“景德镇的瓷土好,画工细,这是‘货好’;但更重要的是,我让船走海路到泉州,再转卖给波斯商人——少了陆路的关卡盘剥,利润能多三成。”他忽然笑了,“做生意就像行船,既要懂水性,也要识风向。”
船行至长江口时,青林终于明白“识风向”的意思。沈万三站在船头,望着往来的商船:“你看那些去高丽的船,都带着松江棉布;去日本的,必装湖州的生丝。为什么?因为高丽天冷,棉布好卖;日本的和服,离不了好丝线。”
青林突然想起现代的“市场调研”。原来六百年前的沈万三,早已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分析供需关系。他悄悄打开投影仪,调出一张明代海上贸易路线图——这是他出发前存在本地的资料。
“先生看这个。”他把屏幕转向沈万三。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着航线:红色是丝绸之路,蓝色是瓷器之路,每条线上都标着货物种类和利润估算。
沈万三的眼睛亮了。他指尖划过屏幕上的“马六甲”:“这里真能转船去西洋?我派去的人总说找不到稳妥的航线。”
“不仅能去,”青林指着标注“胡椒”的节点,“从这里装胡椒回广州,价格能翻五倍。”
沈万三突然抓住他的手腕:“你这图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