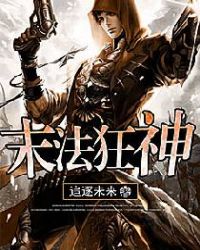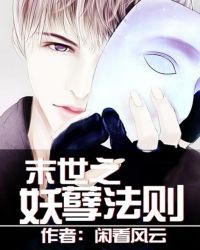古筝小说>开局研究反重力的科技 > 第80章 消失20年,一支粉笔惊艳全场!(第2页)
第80章 消失20年,一支粉笔惊艳全场!(第2页)
他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和系统的未来,成败,就在此一举。
当马英昆站起走向白板时,他那双重新燃烧起火焰的眼睛,让秦卫兵紧握的拳心渗出了汗水。
马英昆没有去看墙上悬挂的、布满复杂公式和模型的全息投影图,也没有碰桌上任何一台终端设备。
在众人惊疑的注视下,他只是走到了那块看似最原始的白板前,捡起了一支白色粉笔。
“你们的思路,被传统托卡马克装置的框架束缚了。”
他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却像一道惊雷,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磁场不是水坝,而是河流。面对湍流,与其拼命围堵,不如因势利导。”
话音未落,他已转身。粉笔的尖端,在光滑的白板上留下第一个白点。
“沙沙……”
粉笔划过白板的沙沙声,仿佛春蚕食叶,孕育着新生。
一组组繁复的偏微分方程从他指尖流淌而出,构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大厦。
他写下的公式如同一条奔涌的逻辑之河,但就在河流即将汇入大海之际,一个冷静而尖锐的声音忽然响起,试图截断水流。
“请等一下,马首席。”
是李振华教授。他站了起来,所有人都从那令人窒息的学术美感中惊醒。
李振华教授直视着白板上的一处,语气虽然克制,但锋芒毕露: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您在这里引入的时变谐振因子,从数学上看堪称绝妙。但从物理实现上,它要求我们对磁场进行微秒级的非线性动态调整。”
“恕我直言,以目前人类的材料学和工程学水平,根本不可能制造出能承受并执行这种指令的超导磁体。这……这是一个理论上完美,但工程上无法实现的屠龙之术。”
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直指理论与现实的鸿沟。许多工程师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这正是他们一直面临的困境。
然而。
马英昆甚至没有回头。他只是用粉笔在刚才的公式旁画了一个圈,沙哑的声音带着一丝洞悉一切的淡然:“谁说,要用一个磁体去承受?”
他转身,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李振华教授身上: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上万个微型磁体单元,构成一个动态的、可编程的磁场阵列?当湍流冲击A点,就由A点附近的单元进行谐振耦合,引导它;当它流向B点,就由B区的单元接力。我们不是在筑坝,李振华教授,我们是在编织一张随波逐流的网。”
“磁场阵列……”李振华教授喃喃自语,镜片后的瞳孔骤然收缩。这个概念,如同劈开混沌的闪电,瞬间照亮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沙沙……”
马英昆没有再给任何人思考的时间,粉笔继续在白板上飞舞。
他不仅给出了理论,更开始徒手推演阵列控制的底层算法和协同协议。如果说之前的理论是史诗,那现在,他正在亲自为这首史诗谱写最华丽的乐章。
没有人再交谈,没有人再走动。整个会议室里,只剩下两种声音:粉笔划过白板的沙沙声,以及在场科学家们因过度震惊而无法抑制的、此起彼伏的倒吸凉气声。
当他写下最后一个参数,将粉笔轻轻放回槽中时,整个白板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公式写满,那是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属于真理的暴力美学。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快……快!输入模型!”之前态度最尖锐的李振华教授,此刻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指着一位年轻的计算物理博士,急切地命令道,“就按白板上的模型,立刻跑一次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