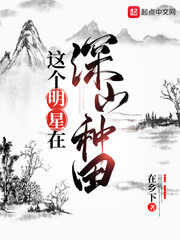古筝小说>侧写师是什么玩意儿 > 第94章 骸骨(第1页)
第94章 骸骨(第1页)
培训进入第八天。持续的高压和昨日的旧案突破,让学员们的气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浮躁褪去,沉淀下来的是一种更加内敛的专注。彼此间的打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实力的初步认可和亟待进一步磨合的团队默契。
王卫国专家站在讲台前,身后投影屏一片漆黑。
“前七天的培训,侧重于对现有信息,尤其是动态信息和物证痕迹的快速侧写。”他声音平稳,“今天,我们将进入另一个层面——面对最沉默的证人。”
屏幕亮起,没有血腥现场,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只有数张高清特写照片:几块沾满泥土、颜色暗淡的人体骨骼碎片,散落在荒草丛生的野地里。旁边放着比例尺。
“案例八。时间,两小时。”王卫国的声音带着一种特殊的凝重,“这是一组模拟案发现场照片,基于真实案例改编,但所有信息均已脱敏处理。你们面对的,只有这些骨头。”
任务显示:
根据骨骼特征判断死者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身高、死亡时间区间)。
分析骨骼表面痕迹,推断可能死因及作案工具类型。
侧写作案者处理尸体的方式及心理特征。
纯粹的法医人类学挑战!侧写的基础,建立在对这堆沉默骸骨的最基础解读之上。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只剩下学员们翻动骨骼特写照片的声响。这对大部分侧写师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
何锋第一时间调出电脑里的法医人类学数据库,开始比对骨骼特征,尤其是骨盆和颅骨的形态,试图确定性别和年龄区间。林薇则专注研究骨骼表面的切痕、刮擦痕和骨折线,试图还原暴力作用的过程。
陈默没有立刻动作。他将所有骨骼照片在桌面上依次排开,目光如同扫描仪,从每一块骨头的形态、色泽、破损程度、附着物上缓缓掠过。他特别注意到了一块肱骨碎片上的几道细微的、平行的划痕,以及几块脊椎骨上不自然的断裂方式。
他拿起笔:
“死者信息:女性,年龄25-30岁之间。依据:骨盆入口形态、骶骨弯曲度、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身高约160-165cm。依据:股骨长度估算。死亡时间:根据骨骼风化程度、土壤附着物及模拟环境温度湿度参数,推断约3-5年。”
“死因及工具:多处骨骼存在锐器砍切痕(刃口较薄,但非专业刀具,可能是家用菜刀类),颅骨有钝器打击造成的凹陷性骨折。死因为致命性颅脑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作案工具至少两种:钝器(如锤子)、锐器(刀)。”
“处理尸体及作案者心理:尸体曾被分解(关节处有尝试性分离痕迹,但手法生疏,未能完全分离)。弃尸荒野,未做深度掩埋,仅简单用杂草树枝遮盖,显示作案者处理尸体时匆忙、慌乱、缺乏经验且体力可能一般。但作案时使用多种工具,手段残忍,显示情绪极度激动或具有爆发性暴力倾向。熟人作案可能性极高(需处理尸体以拖延发现时间,但又不具备完全处理能力)。”
他的报告依旧简洁,却直指核心。不仅完成了基础判断,更一步跨入到对作案者心理和特征的描绘。
何锋的报告紧随其后,在死者基础信息和死因判断上与陈默基本一致,但在作案者心理侧写上更倾向于“情绪失控的陌生人袭击”,理由是对尸体进行分解更符合陌生人试图隐藏受害者身份的特征。
林薇的报告则详细分析了每一种骨骼痕迹对应的力道和角度,推断作案者可能是“右利手,力量中等”,但对作案者与死者关系的判断较为模糊。

![白月光拯救系统[快穿]](/qs_html/img/41/41466/41466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