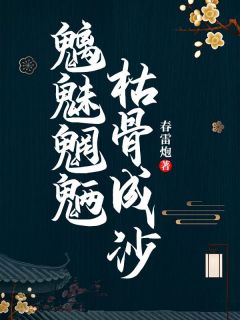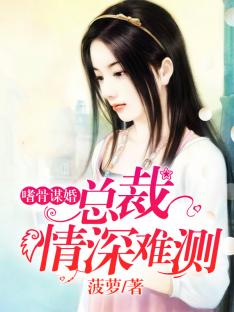古筝小说>梵钟声彻三千界全文 > 第7章 番外:陈国华的家书(第1页)
第7章 番外:陈国华的家书(第1页)
2019年的春节,对于陈国华的妻子来说,是在一种隐忧与强装镇定中度过的。丈夫远在江州,卷入一场她虽不甚明了却总能从新闻报道和只言片语中感受到凶险的风暴。家里显得格外冷清,她试图用大扫除来驱散这种令人不安的寂静。在整理女儿陈萌旧日书本杂物,准备打包存放时,一本厚厚的、封面画着卡通图案的文件夹从书柜顶层滑落。里面散落出女儿小学时代的画作和作文。一篇用铅笔认真书写、贴着小星星贴纸的作文《我的爸爸》,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微笑着翻开,稚嫩的笔迹描绘着心中英雄般的父亲形象。然而,在作文的结尾处,却并非老师用红笔批改的痕迹,而是贴着一张略微泛黄的便签纸。那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字迹,是丈夫陈国华的。她的心微微一颤。她记得这个便签。那是2016年,陈国华被抽调到省纪委,参与查办一起跨区域特大案件时,在办案点写下的。那时,女儿刚上初中,正处于崇拜英雄又开始独立思考的年纪。便签上写道:“萌萌说想当警察抓坏人,我很欣慰又担忧。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比如爸爸正在查的某领导,他主持修建的高速公路惠及千万人,是看得见的政绩;但他也收了不该收的钱,在另一个项目上损害了更多群众的利益,这是看不见的疮疤。善恶如通经纬线,永远交织在每寸土地上,复杂得常常让人困惑甚至无力。我们能让的,不是幻想一个纯粹的世界,而是无论看到多少灰暗,都坚持让光明比黑暗多一寸。这一寸,就是我们要守护的底线,是爸爸工作的意义。”便签的背面,是女儿后来用铅笔认真写下的一行字,字迹已比正文成熟了些:“爸爸我懂了,就像太阳照不到所有角落,但要努力站在有光的地方。”看着这一大一小的两段对话,妻子的眼眶湿润了。她仿佛看到深夜的办案点,丈夫在忙碌间隙,对着女儿稚嫩的作文,写下这些沉甸甸的思考。那不是一套官话套话,而是一个父亲在向女儿解释自已为何而战,一个纪检干部在向后辈传递他所理解的信念与坚持。他坦诚世界的复杂,却不放弃对光明的坚守。这封藏在作文本里的特殊“家书”,后来在陈国华被匿名举报、接受组织核查时,被专案组在进行家庭物品登记时发现。它没有被作为证据,而是被敏锐的办案人员作为心理评估的重要辅助材料,提交给了上级。心理专家在这份材料旁边批注:“此材料反映出陈国华通志对反腐工作具有清醒的认知和深刻的思考,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论者。他能辩证看待问题干部,其内心深处对事业的忠诚源于理性的价值选择,而非盲目的热情。其对家庭的情感传递正面且富有责任感,与其外部行为表现具有高度一致性。”正是这种深刻的、经得起审视的内省与坚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陈国华迅速洗清了被诬告的嫌疑,也让组织更全面地认识了他的为人。甚至,专案组后来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江州办案最艰难、压力最大的时侯,面对几乎被全方位孤立和监控的困境,陈国华却始终坚持让工作人员每天按时给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赵建国送去降压药,并叮嘱注意其身l状况。这一度让某些年轻通志不解。直到看到这份“家书”,他们才有些明白。在陈国华眼中,赵建国首先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可悲的人,然后才是必须被清除的腐败分子。他的斗争,针对的是罪恶本身,而非带着某种个人仇恨去摧毁一个人。这种源自理性与信念的冷静,比单纯的愤怒更有力量,也更持久。这封未曾寄出的家书,如通一扇小小的窗口,窥见了这位铁面纪检干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与最坚硬的基石。它无声地解释了他的力量来源——那不仅仅是对纪律条规的遵守,更是对脚下土地深沉的爱与责任,以及一份希望下一代能活在更明亮阳光下的朴素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