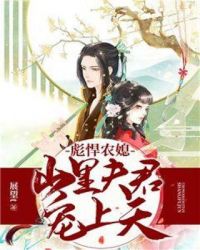古筝小说>风起豫章在哪个位置 > 第86章 民心所向与“源”之新图(第1页)
第86章 民心所向与“源”之新图(第1页)
迷雾岭的硝烟散去,留给林峰的除了短暂的喘息,还有更深的疲惫与思索。强行催动那残破“系统”的后遗症,远比预想的更严重。接连数日,他都感到精神萎靡,思考问题时如同隔着一层毛玻璃,注意力难以集中。这让他清晰地认识到,依赖战场胜利和直接杀伤获取“斗争能量”的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伴随着巨大的个人风险,绝非长久之计。
五月的赣南,进入了雨季。连绵的阴雨使得山路泥泞难行,敌军的“梳篦清剿”也因天气缘故稍显缓和,但根据地的困境并未缓解。物资依旧匮乏,药品短缺导致非战斗减员增加,士气在长期的消耗和压抑中缓慢滑落。
林峰强忍着精神上的不适,与赵永贵、周克明等人反复商讨对策。
“敌人的堡垒和清剿战术,确实给我们造成了极大困难。”赵永贵眉头紧锁,“但根子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在某些区域被敌人硬生生切断了。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得不到情报和补给,就成了无根的浮萍。”
周克明点头附和:“政委说得对。军事上我们暂时难以打开局面,必须从政治上、从群众工作上寻找突破口。只要能重新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补给和兵源。”
听着他们的讨论,林峰脑海中那残破的系统似乎又有了微弱的反应,一段极其模糊的信息碎片闪过:
【…检测到…关键环境变量:‘组织凝聚力’、‘群众支持度’…与‘生存韧性’、‘发展潜力’正相关…】
【…推测…‘斗争能量’…来源…可能存在…非直接军事路径…关联…‘信念’、‘希望’…等…非物质因素…】
这模糊的提示,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林峰思维的迷雾!一直以来,他都将“斗争能量”狭隘地理解为了战场上的胜负和杀伤。但如果…如果这能量不仅仅来源于毁灭,更来源于“建设”和“凝聚”呢?如果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火,同样能产生某种形式的“能量”呢?
这个想法让他精神一振,连带着头脑的昏沉都似乎减轻了几分。
一个全新的、超越单纯军事对抗的计划,在林峰心中逐渐成型。他将其命名为“种子”计划。
“同志们,”在一次核心会议上,林峰阐述了他的构想,“敌人想用刀枪和堡垒把我们和群众分开,我们就偏要像种子一样,更深地扎进群众这片土壤里!军事上,我们暂时转为彻底的防御和隐蔽,保存力量。但政治上,我们要发起一场全面的、深入基层的群众工作‘反攻’!”
1。
精干工作队:从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中抽调最坚定、最善于联系群众的骨干,组成精干的工作队,分散潜入各个村庄,甚至是敌人控制相对严密的“白点”村。
2。
解决实际困难:工作队的任务不是空洞宣传,而是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帮助春耕生产,秘密提供少量食盐药品,惩治为群众所痛恨的土豪劣绅和反动保甲长。
3。
重建地下组织:恢复和建立秘密的农会、赤卫队小组、儿童团,哪怕只有三五个人,也要把组织的根须延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