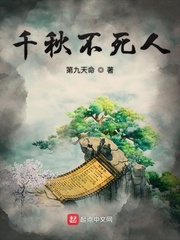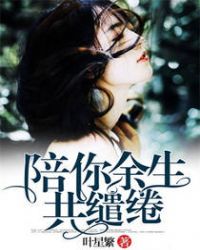古筝小说>民间故事选刊是国家级期刊吗 > 第343章 谁在玻璃外喊妈妈(第2页)
第343章 谁在玻璃外喊妈妈(第2页)
她捡起手机,颤抖着打下一行字:“那……念念妈妈跳湖前,有没有说过什么?比如……听到什么声音?”
这一次,对方沉默了更久。久到林晓以为她不会再回复时,消息来了。
“你怎么知道?听那家的邻居提过一嘴,说念念妈妈最后那两天,精神都不正常了,总跟人说,深夜听见有人敲阳光房的玻璃,轻轻脆脆的,还听见有个小声音在喊:‘妈妈,开开门,外面冷。’”
“妈妈,开开门,外面冷。”
林晓反复看着这行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她记起来了,瑶瑶在梦魇中,也含糊地说过类似的话:“……冷……开门……”
这不是简单的生病。她的女儿,恐怕是真的……撞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被缠上了。
接下来的几天,林晓活在巨大的惶恐和焦虑中。她带着瑶瑶又跑了几家医院,看了儿科看神经科,甚至去看了心理医生,钱花了不少,检查做了一堆,结果都是“无明显器质性病变”、“可能受惊导致神经衰弱”。
瑶瑶的状况时好时坏,但那个苍白的、趴在玻璃上的小女孩影子,似乎在她稚嫩的心灵里扎了根,挥之不去。
万般无奈之下,林晓经人介绍,瞒着丈夫,带着瑶瑶去见了城郊一位姓胡的老人。老人头发花白,眼神却清亮,她仔细看了看瑶瑶的气色,又问了生辰和事发经过,最后轻轻叹了口气。
“孩子年纪小,火焰低,不小心冲撞了。”胡奶奶慢悠悠地说,“那是个‘念想儿’没断的,舍不得走,又找不到妈,看见个灵性通窍的孩子,就凑上来了。”
她让林晓准备几样东西:一件瑶瑶常穿的衣服,三炷安魂香,还有一把崭新的剪刀。
晚上,按照胡奶奶的吩咐,林晓在瑶瑶睡熟后,将她的衣服平整地铺在枕头下。点燃安魂香,青色的烟雾笔直上升,在房间里弥漫开一股沉静的草木气息。然后,她把那把冰冷的剪刀,刃口朝外,轻轻塞进了瑶瑶的枕头底下。
说来也怪,那晚瑶瑶虽然还是翻了几次身,但竟然没有惊叫,也没有再蹬床板。后半夜,呼吸渐渐变得平稳绵长。
第二天清晨,瑶瑶醒来,烧退了不少,眼神也清亮了些。她看着林晓,小声说:“妈妈,我梦见那个小姐姐了……她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我,后来……后来就走了。”
林晓一把抱住女儿,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是后怕,是庆幸,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
胡奶奶说,那孩子(指念念)心有执念,并非恶意,只是迷路了,需要人指引。她让林晓在天黑后,去南边的景观湖边,烧些纸钱,念念往生咒,告诉那对母女,放下牵挂,各自上路。
林晓照做了。那晚没有月亮,湖面黑沉沉的,偶尔有风吹过,带着水腥气。她蹲在湖边,点燃黄纸,火苗舔舐着纸钱,映着她苍白的脸。她低声重复着胡奶奶教的简单咒文,心里默念:“念念,跟你妈妈走吧,别再留在这里了……瑶瑶还小,放过她吧……”
纸钱烧尽,灰烬被风卷起,打着旋儿飘向湖心深处。
自那以后,瑶瑶的烧彻底退了,夜里也不再惊悸蹬床。她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活泼,似乎完全忘记了那段可怕的经历。只是偶尔,在极深的夜里,林晓独自醒来,还是会下意识地看向窗外对面那座阳光房。它依旧在月光下闪着幽冷的光,像一个沉默的墓碑。
关于那对母女的故事,在小区里渐渐沉寂下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偶尔提及、又迅速噤声的禁忌。那户人家很快搬走了,新住户装修时,据说第一件事就是拆掉了那个玻璃阳光房。
生活似乎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但林晓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她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女儿的睡眠,夜里总要起身去看几次,确认瑶瑶睡得安稳。
她常常想起胡奶奶最后说的话:“执念太深,活人受不了,亡魂也走不掉。那孩子(念念)是找不到妈妈,她妈妈……恐怕也一直在找她。”
某个深夜,林晓从浅眠中惊醒,仿佛又听到极远处,传来若有似无的、轻轻敲击玻璃的声音,和一个细弱游丝的女孩嗓音:
“妈妈,开开门,外面冷。”
她猛地坐起,冷汗浸湿了后背。侧耳细听,只有窗外夜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她转头,看向身边熟睡的女儿,瑶瑶呼吸均匀,小脸恬静。
林晓轻轻躺下,将女儿柔软温暖的小身体搂进怀里,仿佛要将所有的阴冷和不安都隔绝在外。
窗外,夜色浓稠如墨。
湖的方向,万籁俱寂。